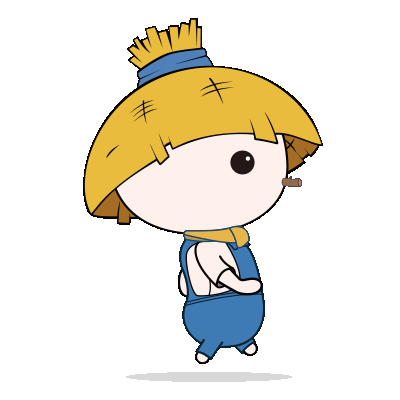嫁了黑切白摄政王(重生)
第22章 从前,有多长
夜, 晚风清冷,缺月高悬。
叶裴瑜伏在太医院的桌案边,身旁点有一盏烛灯, 手握一卷稀世医书,读得颇为入迷。
他是独一个日日夜夜住在太医院的太医, 以他的资历, 本应是个三品, 却因他只接治三公主且未能治愈,得又罪了不少抓尖好强之人, 故自杳贵妃去世以来, 一直是个七品。
木质的门窗被封吹得嘎啦嘎啦响,他轻捏鼻梁,以缓解双眸的刺痛。
怎么办, 这么多年,博览群书, 却找不到可用的法子,若师父健在,定不会如他一般如此棘手。
念起杳淑临死前托付的生生句句, 叶裴瑜便觉得头脑发热颇有些阵痛。
大风刮过, 自窗棂的缝隙处吹来一缕夜风。
叶裴瑜偶尔也会有些不耐。他丢医书到桌上, 仰靠在长长的椅背,一只脚不由翘在桌子的横栏处。
“哎……”
他不明白,同样是心疾, 为何萧元便能恢复地那么好……
����。
忽有异动自窗外传来。
叶裴瑜警觉地提了提耳朵, 只听“刷”地一声,一根袖箭猝然穿破纸窗蹭过他的耳廓。
他一触即跃,极轻松地躲闪开, 一脚踹飞桌案上的香炉。
呛啷!香炉盖掉落,滚烫的香珠飞射出窗,不一会儿传来落地的声音。
轰!
忽有三个黑衣人蓦地冲破大门,叶裴瑜撩起案上烛台在掌中打了个挺,一手扔去。他机警地打开窗户旋身窜出去,三两步跃上瓦,匆匆逃离。
噔噔噔,身后踩瓦的声音穷追不舍,叶裴瑜一袭白衣在夜色中尤为显眼。
啧,真真是飞来横祸。
他心头嘟囔着,身形却潇洒温润地很。
逃命间,一抹脂粉香忽自鼻尖略过,他别过头,瞥见一纤秀的身形闪至他身后,只一甩手,便向后丢出数枚梅花镖:“师兄,多年不见,轻功未降。”
“自西陵离开已十六载,不曾想如今师妹摇身一变,成了三皇妃。”
胸口窜起一呛火烧火燎的怒气,杳窈复杂地瞪了他一眼,与他并肩于皇城上越过一座座殿:“往西侧去,那里正巧无人盯梢。”
“师妹对皇宫的巡逻了如指掌。”
“呵,师兄倒不必阴阳怪气,有什么账,保住了小命再算。”
身后虽只有三名刺客,但对方显然各个都是绝世高手,逼得二人极紧。杳窈面沉地不停向后弹射暗器,却不料对方一一躲过,竟未曾降速:“真棘手啊。”
一黑衣人猝然跳上不远处的高殿,只两息的功夫便与她们并肩而跃。
一根熟悉的银针自侧方、后方两向夹击,杳窈一个飞跃躲过,叶裴瑜却因体力不支,袖子被刮破了一道痕。
杳窈忙吹响口哨。
漆黑的夜幕中,三只利箭从不明方向的天空飞来,箭箭击在黑衣人的脚前,精准击中黑衣人的夜行靴头。
三人猛地挺身停下脚步,其中一人倏然又中一箭,闷哼一声,鲜血淋漓。
“好厉害的箭法!”
“快撤!”
叶裴瑜木着脸,同杳窈飞奔过三个甬道,躲过两队宫女太监与一队巡逻的侍卫,方呼吸促狭地停在皇宫宫门处。
二人趁着夜色,鬼鬼祟祟上了一辆空马车。
“十六年前不告而别人间蒸发,柏师兄可真是有能耐。”杳窈抬手拭去额前的细汗,方缓过气平静些。
好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地使用过轻功了,思及此,叶裴瑜忽勾唇笑了:“十六年,师妹竟嫁入新月皇室,师兄我也颇为敬佩。”
“阴阳怪气。”
“彼此彼此。”
气得牙痒痒,杳窈还要反驳。
那头车帘忽拉开,走进一身着玄衣长袍之人。
他平静落坐于马车的正位,生生将面对面的二人隔开。
一时间,空气竟骤冷。
叶裴瑜眸色中略有讶异,方放平呼吸坐着行礼:“下官叶柏,见过萧王。”
杳窈轻嗤一声:“柏师兄做什么还要维持表面那套功夫?”
“原来,师妹不仅靠上了三皇子,还傍上了萧王?”
“是啊,怎么,十六年毫无音讯,连一个字都不愿同我提起的你,如今见到我有两个大腿抱,眼红了?若非我那日在寮云院恰巧见到了你,还不知你竟化名为叶裴瑜了?”
“裴瑜乃字罢了,我何曾化名?”
“放你的狗屁!”
“师妹说不过便爆粗语了?十六年来没有一点长进。”
叶裴瑜虽面上温和,但望向杳窈的目光与她的一碰,显然电光火石,滋啦滋啦火星子直冒。
那头萧元看不下去,脸猛地一沉,不耐地吐出一个字:“吵。”
杳窈鼻翼翕动一下,气得倒仰。她抱臂靠在马车壁上,时不时瞅瞅叶裴瑜被暗器割破的衣袖:“又是这样,师兄早前也每次皆会因体力十分差劲被师父打得衣袖开花,今日只跑了几段路便气喘吁吁了。”
叶裴瑜低头,方瞥见袖子破了:“嗯,师妹废这么多口舌说道,怕是又想为我缝补一番?”
萧元撑头怔怔望向叶裴瑜的袖子,双眼扬出一道光。
“我为何嫁入新月,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,自会说与你听。”杳窈摊开手,朝他勾了勾,“衣服脱了,我为你缝。”
“三皇子不会泡醋坛?”
“我与他只是表面夫妻……别废话!爱给不给!”
萧元轻咳一声,二人方再度沉默。
“叶柏,你当年放走了胭脂,如今本王将杳贵妃被害之事开诚布公,激怒了林贤妃,方给你惹了杀身之祸。”
“原来那几箭,是萧王射的。”叶裴瑜温文尔雅,一派彬彬有礼的模样,说出来的话却句句带刺,“多谢王爷替下官惹了杀身之祸,还好心救了下官。”
“还有,”少年好似早看透了他,一点也不奇怪地轻唔一声,“三公主身上那瓶药,是本王亲手所制。”
听到这话,叶裴瑜起先一僵,他脑内曾就萧元与芙笙的关系想过多种可能,却唯独没想过这一种。
话题说到祝芙笙的病,马车内又是一片岑寂。
车轱辘一圈圈转,叶裴瑜被直送入萧王府。
他一进门,双眼就直勾勾地盯在地上,一路看过去,满脑袋均是疑问。
萧王府,竟满地都是治疗心疾的药材。
他很难想象长了一张阎王脸,在战场上刀头舐血的萧元,会蹲在地上顶着大太阳种药草、浇水,甚至施肥……
“萧王身强体健,原是因为自学成医术高明的大夫?”叶裴瑜旁敲侧击地打听。
对方冷漠又讥讽:“只比叶太医高明些罢了。”
叶裴瑜被梗住,也不再多说,埋头细细端详每一株稀有的药草。
“除此之外,还有别的,都是这些年来,本王自新月与西陵各地搜集而来。”萧元领二人进入他的书房,手轻轻按在一个玉石上,便显现出一道暗门。
由阿星掌灯,三人入了密室,观得一屋子的奇珍异草。
叶裴瑜环顾一周,心里有了掂量:“这些药草要收集起来,并不容易,起码需要多年,敢问萧王何时开始收集这些药草的?”
“十年前。”
“哦?”叶裴瑜怀疑萧元在诓他,“据下官所知,萧王的生辰与三公主同年同日,萧王如今少年得意,方年岁十五,如何在五岁时便开智着手此事?”
他随意拿起一棵风干了的药草:“下官才疏学浅,却也知此味药对王爷的病并无用处,却是三公主养心丸中的必备草药,萧王竟五岁便为三公主做了这许多?”
杳窈起先以为萧元有收集草药的怪癖,如今结合芙笙所说的字字句句关于那位“与倾”的话,又听到叶裴瑜一通炮轰,方想通了。
她错了,她不该嘲笑祝中林,芙笙妹妹与萧元,许真有那么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
一转念,她不由捂住嘴,竟被萧元感动到,睁大眼睛望向萧元:你五岁就对芙笙如此上心?
她错了,萧元你不是个和尚,你是个情种啊!
“叶太医对本王颇有微词?”萧元一扭头,盯得叶裴瑜犯怵。
周边的气压忽泰山压顶般倒下来,叶裴瑜眉头微皱,紧紧望着那个逼迫而来的少年,好似自己无意间触到了他的逆鳞。
“叶太医即便天纵英才,也没治好她不是么?”
叶裴瑜双眸一颤,放在身侧的双手紧紧握拳:“萧王既然已费心多年,也应知道一些旧事了不是么?当年若非下官,萧王与三公主如今,均不能活,如今的三殿下,均是下官苦心助其拖命的成果。”
成果?
少年的笑意有些疏冷,尾音竟有些发颤:“今日终与叶太医对峙,还请叶太医言明,景丰三年的所有细节。”
……
景丰三年,冬日。
一声婴儿的啼哭,骤然划破夜的寂静,随之而来的,是萧王府立一叠叠的生死状。
那晚,得到消息的米公公,焦头烂额地奔向景华宫。
“回陛下,萧王府的小世子诞了。”
“此等闲事,也来烦朕?滚!”
“陛下,天降不祥呐,”米公公四脚并用,爬几步凑上来,压低声音道,“小世子,胸有双生之心,国师预言,大恶降临,不详啊!”
“什么……双生心?”
祝靖尚未有所反应,龙床上的杳贵妃登时吓得花容失色。她惊呼一声,竟生生倒入祝靖的怀里。
她正怀着肚子,亦近临产,如今听了如此骇人之事颇受刺激。
米公公的冷汗浸了衣襟,他盯着眼看喘不过气的杳贵妃,只见一缕殷红自她的里裤流下,滴滴答答落在他的跟前。
“爱妃,爱妃!”祝靖不知所措,转头甩了米公公一巴掌,“还不快召太医!”
景丰三年,十二月十二日子时,萧王府小世子出生,取名为萧元。
辰时,皇宫清月楼内,三公主出生,取名为祝芙笙。
大雪越发肆虐,于重檐翘角上积了拳头般厚。
“陛下,陛下恕罪啊陛下!”
自清月楼内,拖出不知第几个太医,他声嘶力竭哀嚎着,于院外整整挨了四十大板。
数不清的宫女太监和太医哭爹喊娘,上有老下有小的说辞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重复,声浪一波接着一波。
剩下的太医们颤栗地跪在清月楼内,脑门贴地不敢吱声,抖和成一团,远远看去像一群铁锅上的肉圆。
米公公立在一旁,偷偷瞟一眼太医院众人,低头不敢吱声,帽尖因他不自觉的颤栗晃得不像样。
骇人的寂静下,唯有年轻的叶太医澹然正立,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模样。
倏然,他上前一步,郑重磕头:“陛下,臣斗胆。贵妃娘娘早产致三公主心衰,本应夭折,然臣有一计,还请陛下先恕罪,方敢言之。”
米公公转头又瞄了一眼襁褓,三公主小小的身躯此时因呼吸不畅而起伏,弱小的生命挣扎不息。
上言:“恕你无罪。”
“既然萧世子多了一颗心,陛下不妨‘借’来一用。”
这家伙莫不是疯了?
米公公一眼瞪过去,清月楼一应人等均被叶太医骇人的言辞震住,看鬼似的。
宫女们率先回过神,纷纷垂脑袋装鹌鹑。房内一排太医像鸵鸟,恨不得把头埋入地下。就连早前自称稳如泰山的针灸神手,也颤得跟老寒腿似的。
天底下,哪有此等换心的先例?
谁敢找死出头,嫌活的不够长?
“若失败,当如何。”
帝王威压泰山压顶而来,米公公吓得连忙跪下。
他再看那叶太医,只见少年人抬起头,不惧的余光默默瞥了眼正在榻上淌眼抹泪的杳贵妃,坚定道:“臣师从‘西陵华佗’,以自身性命与九族担保,有必成的信心。”
座上祝靖小胡子一挑:“来人!召萧王、萧王妃、萧世子即刻觐见!”
那一晚,自清月楼出来的盆殷红了后院的花。叶太医也因此被升为四品。
此后不久,祝靖诏曰,念在萧王为国征战数年之功,仅收归他的军权,并将其全家发派远山,五代不得回京。
然,自萧王一家出了天京,景华宫的夜,再不得安宁。
祝靖心虚不安、良心未泯,许是那晚情形深刻印在脑海挥之不去,于梦中反复重映,他常年在午夜经受万蚁攀心、蚀人魂魄般的痛苦。
那晚,他生生以萧王府上上下下几十口人乃至萧嫔的性命,威胁萧翊交出萧元。
那晚,他让萧王夫妇二人,亲眼望着自家幼儿活活被叶太医开膛破肚,强取一颗鲜嫩的心。
“国师,朕,这是怎么了?”
半夜,祝靖将国师召来,满是虚汗的手拽住他的袖子一迭连声地催问。
“陛下,”国师行礼,缕缕长髯,一字一句恭敬道,“萧元一颗心,给了芙笙公主。芙笙公主虽流着陛下的龙之血脉,可压制其黑暗的恶性,然公主年纪尚小,无法将其彻底铲除,故梦魇了陛下。
陛下须得忍痛割爱,将芙笙公主看押在天京郊外,及笄之前,不得入京。知道此事的奴才们,也均不能留活口,免得陛下英明毁于一旦呐。”
“妥……妥!”
景丰六年,皇宫大内,太监、宫女、太医,一下子腾出许多空位。
一日,祝靖忽派人闯入清月楼,从杳贵妃手中抢走三岁不到的三公主,将其“圈养”在天京郊外的沁芳园,不惜派重兵把守。
他狠心下旨:谁若让三公主离开沁芳园一步,满门抄斩。
那一年,雪连下了半月,冷入人心。
……
明明是春日,今夜却有些出乎意料地凉。
芙笙有暇读话本累了,方用铜盖盖灭一盏灯。
窗外有异响,似有人翻墙。
是与倾么?
可他来,从没这么大动静。
芙笙如远山含黛的眉眼微敛,顺手披上天香色的外衣,推开卧房的窗,便见那梨花树下,踉跄走来一个玄衣�裳的儿郎。
“与倾?”她轻唤他。
“嗯,还未睡?”
“正要休息。”她手指绞着衣袖思索一番,还是戳破了这道窗户纸,“与倾,我……知道你是谁了。”
对方一愣,须臾,方淡淡唔一声。
“我已将叶太医安顿妥当,这几日你若身体不适,便告知清风,我会速派人来。”
“好。”目光向下,芙笙忽瞥见他袖子边的划伤,“你受伤了?”
“未曾,只不小心划破了外衣。”他似在期待什么,声音又轻又飘。
芙笙这才发现他穿的并非从前常穿的那件带兜帽的夜行衣,只是套了个兜帽披风罢了,应是今日白日里穿的玄衣。
“既如此,你褪下予我罢,我得空帮你缝补缝补。”
“好。”
闻言,少年人就等这句似的,忙将外衣褪了给她。
衣服略重,质感顺当,还带有少年温热的体温。
芙笙将其抱在怀中,不禁红了面,有些局促。
“舅父……”
“萧元。”
“嗯……萧元……你为何要叫与倾呢?”
他抬起白皙的手,取下兜帽。莹莹月光下,清秀又冷峻的面庞竟蒙上好几分泾渭分明的温柔:“与倾是我的字,我用了好多年。”
“噗嗤,”芙笙笑了,“你也不过与我同岁,又未及冠,哪有好多年?”
他忽抬手,未触到芙笙的面,却在空中虚描她的眉眼:“好多年,数不清的好多年。”
从上上辈子,用到这辈子,只是你从来都不知道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