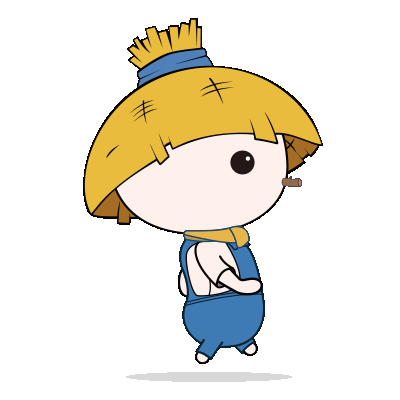娇靥如花
第72章
他的指腹擦过寒酥的耳朵尖,带来一点温热。那一缕随风不安分轻摇的发丝在他指下乖顺地躲在她耳后。她慌乱飘摇的心也慢慢稳下来。
封岌收回手,将为数不多的两块柴木扔进火堆。
木柴偶尔噼里啪啦地响一声,在寂静的夜里,在沉默的两个人之间显得异常清脆响亮。
好半晌,寒酥才平息了落泪,轻轻转过脸去,望着徐徐燃着的火苗,望着落雪义无反顾拥抱烈火又葬身于烈火。
她不知如何面对封岌,歉意低声:“是我连累将军。”
“这话不对。”封岌反驳,“他们因我而挟持你,你是被我连累。”
寒酥慢慢抬眼望向封岌。她眼眶里还有泪,微湿的视线给封岌蒙了一层不真切的温柔之意。
有很多话堵在寒酥心里,不是她不愿意与封岌说,而是她自己也没有理清头绪。
她只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――她能给封岌什么?她一无所有,什么都给不了他。
长舟又从院外进来,禀告:“将军,圣上亲自带着禁军来到青柳县,正往善堂的方向去。”
封岌脸色顿时微沉。他略思量,下令:“立刻将我母亲从善堂接走。”
“是!”长舟转身就走,刚迈出一步又停下脚步。他转过身望向封岌,迟疑询问:“将军,您的伤……”
“无碍。”封岌面色如常道。
长舟打量了一下封岌神色,不再说其他,脚步匆匆地往山下去。
封岌收回视线望向寒酥,发现她还看着他胸口的伤处。
“将军,我们什么时候下山?找大夫给您处理了伤口才好……”寒酥道。
“这雪恐怕要下起来。天黑山路不好走,我们等雪停再走。要起风了,我们进屋里去。”封岌站起身,朝寒酥伸手。
寒酥朝封岌伸出手,恰巧有一片雪落在她手背上,带来一阵凉意。等她将手递放在封岌掌心,顿时感觉到他掌心的温暖。
这处土匪窝早就废弃,处处破败得不成样子。封岌熄了院子里本就将要烧尽的火堆,然后在院子里找寻一番,找了个窗扇完好的屋子。那里面还留着这伙刺客居住过的痕迹。
封岌怕寒酥怕黑,他寻到唯一的一根蜡烛将其点燃,漆黑的内屋终于亮起来,虽然烛光十分微弱。
寒酥在屋子里找了找,找到了水,却因为是那些杀手留下的东西,不敢用。她转头望向封岌,见他将身上的外袍脱下来,铺到石板床上。
她朝封岌走过去,再次蹙眉问:“真的不用现在就寻大夫吗?”
“不用。我歇一会儿就好。”封岌坐在石板床上,倚靠着床头墙壁,闭目养神。
寒酥立在一旁,不敢乱走动吵扰了他,时不时望向他胸前的伤处。纵使避开了要害,可确确实实整个匕首刺进去,伤口多深啊!
封岌睁开眼睛,他对寒酥笑笑,道:“别傻站着,上来歇一会儿。”
寒酥点头,在他身边坐下。封岌伸手揽过她的腰身,将人带进怀里。他温声问:“有没有害怕?”
寒酥诚实说:“有一点。”
封岌摸摸寒酥的头,手掌托着寒酥的头侧,将她摁在他胸膛让她靠着。他哄慰:“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说话如下令的人,安慰人时言语之间的力量感,总是那么让人踏实安心。
寒酥难得乖顺地偎在他怀里,不含目的与演戏。
她的眼睛一直是湿的,她很努力克制不落泪。她靠在他怀里,距离他另一侧胸膛上的伤口更近了,一双眼睛便更不舍得离开他的伤处,始终担忧着。
封岌发现了。他伸手,宽大的掌心捂住了寒酥的眼睛,道:“闭上眼睛休息。”
寒酥的视线一下子暗下去,一片黑暗却并不令人心生恐惧,是另一种深沉的安全。
一些没能忍住的眼泪,悄悄染湿了封岌的掌心。
窗外有风雪,只一根蜡烛微弱点亮的昏暗屋子里,两个人依偎在一起,都浅浅地睡着了。寒酥睡时手也捏着封岌的衣角没松开。封岌捂在寒酥眼睛上的手掌也一直没放下。
窗外的降雪没有要停的趋势,反倒是风声呼啸起来。
本就睡不沉的寒酥立刻醒过来。
“将军?”她轻声唤。
没有回应。
寒酥小心翼翼地捧着封岌捂在她眼睛上的手,将它挪开。她在他怀里抬起眼睛望向他,却惊愕发现封岌脸色苍白。
寒酥大惊,立刻颤颤伸手,将手心贴在封岌的额头。热度烫了寒酥的手心。
他发烧了!
寒酥一下子坐直身,心头狂跳。他什么都没说,可必是很不舒服了才会说想要歇一会儿。
封岌亦未睡沉,他未睁眼,开口:“无碍,我小睡片刻。”
他仍旧用温和沉稳的语气,可寒酥听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疲惫。
寒酥说好,安静地坐在他身边。
他面不改色地将匕首刺进胸膛,紧接着又从容地安慰她、下令交代长舟事宜,就像没事人一样。从始至终,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。
可是那么深的伤,怎么可能没事!再如何无所不能的人,他也是人啊!
寒酥又掉了眼泪,她仍旧没有发出声音,泪水无声坠落。她时不时查看一下封岌的伤口,又时不时试一试封岌的额温。
他说他想小睡片刻,寒酥不敢吵扰了他,但是又担心他睡着了不好。到后来,她明显感觉到封岌睡沉了。她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。
寒风从门缝窗缝溜进来,带来一阵阵寒气。
寒酥走到窗口,仔细去听外面的响动。她在心里盼着长舟早些回来,她一个人待在封岌身边只觉得自己没用,什么都帮不上他,束手无策的滋味让她太难受了。
寒酥突然反应过来,她将身上的外衣解下来盖在封岌的身上,又小心翼翼去抱着他,企图给他些许温暖,让他不要冷。
又过了好一阵子,直到屋内唯一的那根蜡烛也将要烧尽,寒酥听见外面有脚步声。
难道是长舟回来了?
寒酥急急忙忙起身,冲出门外去找长舟求救。
可是她站在门口,生生停下脚步,警惕地盯着来者――黑压压的一群人,个个冷着一张脸,手握腰间佩刀。
寒酥怀疑这些人不是封岌的手下。
是什么人想杀封岌?宫中人吗?会不会是幕后主谋因派杀手刺杀不成,又有后手,直接带人围堵而来?
寒酥觉得一定是这样!要不然将军刚刚听长舟禀话得知禁军赶往善堂时,为何令长舟将老夫人立刻转移走?
为首的头领扫了一眼院中的尸体,冷声询问:“赫延王可在?”
他这样一发问,寒酥立刻笃定他们不是封岌的人。封岌的部下只会尊称他“将军”,从不唤他赫延王!
怎么办?
将军昏睡着,长舟也还没回来。
怎么办?
寒酥垂在身侧的手颤了颤,染着泪的眸光晃动,可是茫然很快在她眼里消失,换上决然。
她要拖延时间等长舟回来。
她弯腰捡起地上的一把长刀,这是杀手留下的刀。
寒酥望着一步步靠近的禁军,慢慢举起手中的刀。
她的神明病了伤了,纵使她什么都阻止不了,她也要站在他身前。
所谓勇气,不是能做多了不起的事情。而是明知不可为时,豁出一切的逆行。
长刀沉甸甸,寒酥艰难紧握高抬。
她手腕酸痛快要握不住的时候,在她身后伸出一只手来,覆上她的手背,抚慰般轻握一下。熟悉的温度让寒酥微怔,急忙回头望去。
封岌站在他身后,脸上的苍白已消。
封岌拿走了寒酥手中的刀,望着庭院里的禁军,沉声:“刘统领何事?”
刘鸿波怔了怔,目光在封岌和寒酥之间游移了一下,而后道:“属下奉圣令前来接赫延王。”
封岌不急不缓道:“替我问圣上安康,夜深路遥,不打扰圣上安歇,明早参见圣上。”
“这……”刘鸿波迟疑起来。
封岌沉声再道:“不送。”
这是明显的逐客令。刘鸿波迟疑了片刻,咬了下牙,颔首道:“好!”
他挥了挥手,带着属下转身离去。整齐划一的步履叩响寂静的山中夜色。
封岌将手中的刀随意放在一旁,伸手握住寒酥的细腰,单手将侧对着他的寒酥转过身面朝他。
他垂眼看他,深邃的眸底温和柔意。他说:“不是与你说过了?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他在,她不需要为任何事害怕。
寒酥抬手,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泪,又急急忙忙伸手去摸封岌的额温。还有一点余热,倒也的确退烧了。
他好像没事了。可一想到他发烧前的从容不迫,寒酥一时不敢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没事了。
她惶惶望着他,眼底担忧藏不住。
封岌撑在后腰的手掌微用力一送,就将寒酥单薄的身子摁进怀里。他手掌从寒酥的后腰慢慢上移,抚过她笔直纤细的脊背,轻捏了一下她的后颈,最后抚上她的后脑,轻轻地摸一摸,将人送到怀里,让她额头抵在他胸膛。
寒酥眉心抵在他胸口,她垂着眼,眼泪掉下来。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泪落在他的衣摆上。
“寒酥,你哭的时候没有必要忍着不出声。”封岌拉住寒酥垂在身侧的双手,指引着她帮着她让她来抱住他的腰身。
寒酥闭上眼睛,环在封岌腰后的手轻轻交握。
寒风呼啸呜咽,藏着寒酥小声的啜涕。
封岌垂眼看寒酥,她在他怀里小声地哭,看上去娇小柔弱。可是他眼前浮现寒酥费力举着重刀站在门口挡在他身前的身影。
封岌低下头,将一个很浅很浅的吻落在寒酥的头顶。
寒酥哭了一会儿,将憋在心里的惧哭尽,很快收了泪调整了情绪。她别开脸擦去眼泪,又是清冷沉着的表情。她轻轻去拉封岌的衣襟,去瞧他的伤口。
她蹙眉抬眸,望着他问:“您为什么要这样做?既然已经暗中派人围了这里,直接射箭就是。”
“都是最顶尖的杀手,他们一时的懵怔是最好的下手时机。否则他们一直警惕着,纵有百步穿杨的准头,也难保有人提防反应。”封岌用指腹捻去寒酥眼角沾的一点泪,“免得架在你肩上的刀一抖,伤了你。”
他说的都很有道理,可寒酥还是觉得这一刀不值得,很不值得。
封岌将沾了一点的泪的指腹放在唇上蹭了一下,道:“走吧。下山去。趁着现在没有雪。”
可是两个人运气不太好,刚走出山上的土匪窝,往山下走了没多久,又开始下雪。不仅是下雪,灰色的硕大雪花里时不时夹杂着冰雹。
一时间冰雹砸落的声音清脆连连。
封岌一手将寒酥护在怀里,一手撑着压在寒酥的头顶,带着她快步往前走,寻到一处山体凹陷处。
从远处看像一个山洞,两个人走进去才发现像是山上土匪挖出来的。可是挖了一半,也不知道他们原本打算干什么。
凹陷进去的地方并不大,两个人挤进去堪堪能够避身。封岌让寒酥先进去,他高大的身躯立在外面,几乎为寒酥挡去了所有的寒风。
寒酥从封岌的颈侧往外望去,双手抱住封岌的腰侧,攥着他的衣角往里拽了又拽。
“我已经完全贴在你身上了,再拽要把你压扁了。”封岌说。
寒酥仍踮着脚向外望,生怕那些风雪和冰雹伤了封岌。她问:“您能不能实话与我说,您真的没事了,而不是在逞强?”
封岌刚欲开口,寒酥又抢先再道:“千万不要再前一刻好好的,下一刻突然就……”
她抿起唇,尽力也忍泪。
“我确实没事了。”封岌郑重道,“寒酥,不要怕不要哭。我没有骗过你。刚刚也没有。确实只是需要稍微休息一下,就会无碍。”
寒酥微仰头望着他,她用力抿着唇,抿得唇线发白,倔强的模样惹得封岌怜惜。他垂首靠近,去亲她紧绷的唇线。
明明都很冷的两个人,却是双唇相贴时,霎时有暖流荡过。
一个本来怀着安慰意味的轻吻,突然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唇齿相贴相吮相磨至不可分你我。外面呼啸的风声藏着凹陷里的深吻。
许久后,焦灼的深吻突然又变得轻柔缓慢。封岌轻轻亲了一下寒酥的唇角,而后柔吻从寒酥的唇角悄落,辗转落在寒酥如雪的颈部,他小心翼翼地去吻寒酥颈上被刀刃划到的小伤口。她脖子上伤口周围有一点血迹,被封岌缓慢尝进口中。
她身上就连鲜血,也是甜的。
寒酥颈部的划伤处因封岌而微疼与微痒纠绊,惹得她身子不由不自然地紧绷。她眼睫轻颤,望向封岌。她看着他俯首垂眸于她身前,看着他经过岁月打磨后仍不失棱角的眉宇。她视线下移,落在封岌微动的喉结。
当封岌离开她的划伤,刚抬首,寒酥踮起脚尖,将唇舌贴在他的喉结。她又轻扯封岌的衣襟,指尖微颤着抚上他坚硕的胸膛。
男女之间的感情在寒酥心里向来被放在很低的位置,可是压抑了太久的情愫,终于找到一个宣泄口,有些事压抑太久,终要失控。
寒酥理智知道自己的荒唐无耻,是因为半月欢吗?她算了算,似乎是第十五日到了吧?在这一刻,她竟然有些感谢半月欢。
封岌垂眼看她,眼中却浮现一丝诧异。
不合时宜的冰雹只敲落了片刻,便消失不见。肆虐的寒风也逐渐温柔下来,唯独落雪还在纷纷扬扬,似要洗刷掩盖什么。